作者:小貨貨
求人不如求己
民國65年的春節,母親利用拜年的機會,四處奔波打探,看看父親入獄後,那些地方需要打點,老哥則沒在家待過,而我哪都不想去,基本上成了個宅男。元宵節那天,老哥突然在家中出現,但不知他在這花花世界中,到底遭遇了什麼,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回家和我說話的次數,用不到一隻手就數完了,吃完元宵後,我這位偉大的老哥,四平八穩的倒在床上,瞬間便呼呼大睡。
那晚,母親把我叫到她身旁,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小弟,媽媽這幾天造訪了許多親朋好友,有的我和你父親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曾幫過他們,有的和我們也有多年的交情,但這些人要不就是用無關的藉口來搪塞我、要不就是避不見面,讓我深深體會感到人世間的冷暖無情,但我並不怪他們,終究誰也不願和匪諜的家庭沾上邊,此一時、彼一時,如此的情境,我們心中有數即可,無需強求。”
其實母親和我講的這番話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我已有所感覺,雖然那時我還是個高中生,年長的街坊鄰居並未把我放在眼裡,但他們多少都曾叮嚀過自己的兒女,儘量不要與我們家接觸,縱使大家不明說,但心理都有底,心照不宣而已。
這段經歷對我人生的成長,有著極大的影響,從小母親教誨我要以誠待人,她說我們家人丁少,在台灣沒有親戚也沒有祖業,需要靠朋友幫忙的地方很多,因此倘若有人需要幫忙時,在能力範圍內,我們要義不容辭,且無需要求任何的回報,如此我們才能逐漸積累人脈,日後若是有需要他人幫忙時,才不會到處碰壁,所謂“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道理,實乃如此。
父親一事也讓我深深體會到何謂“知心朋友”,求人不如求己,無需怨天尤人,上蒼量給每個人的生命,都有所不同;對我而言,在尚未成年時,就碰上了一樁無法想像的噩耗,雖與生死無關,但無名的指控,卻經常壓著我喘不過氣來。記得事情剛發生的幾年中,我常在夜深人靜時,看到母親拖著疲憊的身體,獨自坐在院中的藤椅上,兩眼無神地望著天空,那是一份無言的宣洩、更是一種無淚的沮喪。
母親一生的命運,坎坷不平,16歲為逃離日本人的打壓,隻身離開東北老家,抗戰勝利後,短暫返家後,又離家到長春就讀中學;共產黨接收東北後,母親隨學校南遷,逃難時多次從死裡逃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來到台灣,與父親結婚成家後,原本希望能平平凡凡的過日子,誰知老天爺還是不放過她,接二連三地將無情的重擔,丟在她的身上,直到她躺平為止。

高二下學期開學後,我天天都盼望要趕快長大,如此便能幫助母親拖離苦海,有時更希望日子能過的飛快,某一天父親會突然出現在家門口,一切都恢復到從前,全家和樂融融。然而不久我便領悟到這將是段漫長的日子,只是對一個17歲的高中生,我又該如何在短時間內克服這樣的挑戰,解鈴還需繫鈴人,最後我靠著籃球場和舊書攤的陪伴,走出了這條死胡同。
許多高中的同校同學,高中時我並不認識,但數十年後,我常會遇到曾是同所高中的同學說認識我,因為他們記得當時有個胖子很會打籃球,上了球場後,橫衝直撞,健步如飛,宛如行雲流水,摸不著邊際,一個胖子能如有如此的身手,他們自然印象深刻;然而真正的原因是我在打球時,便會將那些惱人的事全部拋於腦後,可以算是一種逃避、也可以看成是是短暫麻痺自我的解脫!
身體的疲憊畢竟只是暫時性的,要真正能從這深淵谷底中走出,心靈上的復甦,斷非是在籃球場上飛奔幾次就能解決的問題,每當午夜時分,我內心深處的苦楚、憤怒與不甘,總會如排山倒海般地一次又一次的湧上心頭。記得小時候,父親常對我說:“舜和人也、予和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這句話偶爾也會在我的腦海中浮現,但對於我當時的處境,這句話還能派上用場嗎 ?
放學打完籃球後,我常獨自徘徊在牯嶺街的舊書攤中,試圖在一籮筐的舊書堆裡,尋找蛛絲馬跡,期盼我能找到解決的辦法,但總是事與願違、鎩羽而歸,可是我就是不認輸,認定就是因為我能力不行,功夫下的不夠深,所以才無法在書中悟出道理。
所謂勤能補拙、儉以養廉,那時我的夜生活不是上補習班,而是在舊書攤內的層層書籍中,尋找人生的真諦和意義,我要的不是解脫,而是要理出重新啟動人生的方法,那時我所面對的不是“生存”的挑戰,而是“存活”的關鍵,我們全家必須要先能夠“苟活”,才有資格尋找“存活”的方法,其他都不是重點。
我高中一半的光陰,便是在強制消耗體力後,心中反覆論證我該何去何從下度過,如此日以繼夜、勞心勞力的挑戰,讓我經常疲憊不堪,上課成了形式,而我則成了個裡外不合、靈魂不一的肉體;當時不流行什麼憂鬱症,雖然我常提醒自己絕不能掉入這個萬劫不復的坑,但還是背著這個緊箍咒,醉生夢死地走完了高中的生涯!
良師益友
民國64年底在飯館與調查局外勤人員的一席話後,我按照他的建議,第二天就到教官室申請加入國民黨的青年黨部。當時想其實入黨也沒什麼大不了的,頂多就是參加一些言不及義的研討會,但倘若如此就能甩脫被閒雜人等的跟蹤,至少可以活的自由自在些,何樂而不為之。意料之外的是宣誓入黨後,除了沒有固定的活動外,甚至也未接獲任何的指示,久而久之,這個無厘頭的黨員,便被我拋在九霄雲外,好像啥事都沒有發生過。
高二下學期開學後不久,班導告知訓導處訓育組的周組長找我,當時我自認沒犯什麼錯,便坦然前往。到了訓導處,迎面來的是一位50歲上下,身高一百八十多公分的中年人,他滿臉笑容,灰白的鬢髮,和藹可親,說話時的河南口音和幼年時巷口饅頭店的郭老闆,如出一轍、倍感親切,也讓我們首次的談話,在一遍歡樂聲中,侃侃而談的度過。
周組長對我說:“高中教育在學科外的課外活動,並不侷限在校內社團和校際比賽,還有許多青年救國團辦的活動,其中有幾個訓練營,原本是針對大專院校的學生所設計的,目的是希望能從年輕的一代中,培養出未來社會的菁英領導,今年每所高中可以推薦2位學生,經過甄選核准後便可參加。時間主要是在寒暑假的期間,不會耽誤功課,你考慮一下,如果願意參加再通知我,不必勉強。”
在現實社會的今天,“良師益友”漸漸成為客套話的說法,但周組長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出現,雖然我仍不知道當時他對我的狀況了解有多少,尤其是父親的案件,但每次與他交談,我總能在心靈上得到一劑強心針,燃起我勇敢面對現實、繼續活下去的動力。
在當時以升學為主的教育制度下,周組長是位被邊緣化的老師,因為他教的科目是公民與道德,既然大學聯招不考這個科目,一般學生對於這門課的重視程度,自然是極低。但周組長在授課時以及課後的交談上,依然會耐心和學生溝通,倘若同學們能靜下心來聆聽,在其言行字語之間,可以發現很多做人做事的真理,特別是對我這名心中充滿怨恨、疑惑人生的“問題學生”而言,有如萬靈神丹、藥到病除,受益良多。
經由学校的推薦,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參加了救國團主辦的康樂輔導營,是少數入選的高中生之一。那時救國團在寒暑假所主辦的活動,在各大專院校和高中都非常熱門,例如虎嘯戰鬥營、中橫谷關行、東海岸健行隊及澎湖戰鬥營等,都是搶手貨,一旦開放申請,瞬間就會額滿,一票難求。而救國團康樂輔導營成立的主旨,便是培訓在寒暑假主辦各種活動時的領隊和駐站人員,因此參加康輔營受訓的學員,主要來自於各校學聯會的幹部及社團負責人,從群眾組織和團康領導的角度來看,每個學員都是菁英、人人均有獨當一面的本事。

只是當時我對康輔營並無任何概念,僅從海報上的簡介,對其略知一二。整個訓練營歷時十天左右,課程的規劃、井然有序,學員在報到前,已事先被分組,前半部的訓練以理論為中心,闡述如何建立小組成員彼此間的默契,期間也會穿插各種團康活動,讓整個訓練營的氣氛隨時保持在高昂的狀態中。
後半部的訓練則以學以致用位為主,除了舉辦各組間不同類型的競賽外,刻意在結業前,安排了一次訓練營外的實習,利用附近中小學校的返校日,讓所有的學員能夠實際參與,從而模擬日後若成為救國團活動中的領隊或是駐站人員時,該有的團康組織力及執行力。
這個康輔營的構思與設計,源於當時救國團活動組內的一位編審,幾年後晉升為專門委員,大家稱其為張老師;張老師畢業於師大物理系,不知是何因緣際會,他在畢業後從一位物理老師,搖身一變,轉業成為了團康的專家。張老師同時也是土風舞的高手,當時各大專院校的土風舞社,鸞翔鳳集,集結了許多姿色美麗的女同學以及英俊瀟灑的男同學參加,群英薈萃,美女俊男翩翩起舞的英姿,美不勝收,成為許多人美好的年輕回憶之一。
只是對於我這位心寬體胖、五音不全的高中生而言,當我體會到這個特色時,便自知是來錯了訓練營,如此美輪美奐的團康活動,可能會因為我的出現而大煞風景、破壞了所有的氣氛;不過既來之則安之,我只要能安然度過這個訓練營,結束後能向周組長有所交代,便算完成任務了。
那次的訓練營是在中國文化大學位於陽明山的校本部舉行,晚上就寢前的自由時間,我都會在校園內尋找一處可以俯瞰台北盆地的地方,舒緩我緊繃的心情,雖然那時離父親的判決已有半年以上,但政府相關單位並未告知父親被發監至何處,而每次母親前往詢問時,都會得到同樣的答案,那就是在確定後會立即通知我們。
終究父親已被判刑,鋃鐺入獄,姑且不論是否是冤獄,難不成就是因為被定性為匪諜罪,一切只能聽從司法機關的指令,非但上訴無門,連家人想要知曉受刑人下落的權利都被剝奪,至今我都無法了解如此作業的邏輯為何,“這些基本的人權,匪諜家屬不配也不允許擁有”,這是當時我唯一能夠想出的解釋!
話說回來,在繁星滿天的夜晚,從山頂居高臨下俯瞰盆地的夜景,的確可以舒緩鬱悶的心情,讓我能毫無約束的遐想,腦海中便常常浮現出小時候父親處罰我的情景,歷歷如新,那時真希望這段不是很愉快的經歷能夠重演,就是再被父親處罰多少遍,我都願意。父親生於民國二年,倘若沒有提前假釋,等到他服刑完畢回家時,應該已是74歲的老人了,每次想到這裡,我的眼眶都會濕潤,這是家門的不幸,還是老天爺不公,專門戲弄一些無法反抗的家庭,進而彰顯其權威呢 ?
訓練營快要結束的前二天,我照例找了一處可以俯瞰台北市夜景的地方,那天下著毛毛雨,我只能退至可以擋雨的台階上,坐下前我深深地吐了口大氣,舒緩心中積累的壓力。我剛坐下,身後傳來一個聲音:“有什麼嚴重的事,會讓一位高中生有這麼大的嘆息聲呢 ?”
我回頭一看,發現問我的是訓練營的負責人張老師,其實不管是誰在那段時間內,問我類似的問題,我都不會正面回答,但我又不想胡謅個原因,主要是因為父親常告誡我,每當你說一句謊言,就需要用更多的謊話來圓這個謊,所以我的標準回覆,一律都是“家中遇到些麻煩事,母親正在盡力解決,相信不久便可以解決!”
張老師不愧是籌辦活動的專家,一聽就知道我是在顧左右而言他,但他也不拆穿我,甚至還在台階上坐下,和我天南地北的閒聊,讓我的心情比往常有了更多的舒緩。接下來的五年,每年的寒暑假,我都會支援張老師主辦的各種不同訓練營,直到我大學畢業出國留學為止。
張老師是我成長過程中的一盞明燈,雖然我從未將父親的事告知於他,他也從未問過我,但在應對突發事件時需有的策略邏輯、做為領導核心時該有的運籌帷幄、以及策劃執行方針時應有的縝密思維等方面上,張老師利用訓練營實際發生的狀況,對我進行機會教育,在潛移默化中,裨益我在日後創業時,能適時洞察市場的詭辯,從而快速調整經營的步調和策略,是我永難忘懷的恩師。無奈張老師英年早逝,四十多歲時,因肝癌而辭世,天妒英才、溘然辭世。
屋漏偏逢連夜
父親的審判定讞後沒多久,母親就對我說:“你想考醫學系的想法,可以就此打住,由於你父親的事件,你們兄弟二人想要在台灣發展,成功率極小,這份匪諜家庭成員的大帽子,不知道會跟著你們多少年,倘若你想在公家機關或是公立醫院發展,這個無形的殺手將會成為最大的絆腳石,這點務必要切記。”
綜觀當時的主客觀環境,母親如此的推理,無庸置疑。母親還告訴我,當下唯一的出路便是出國留學,離開這個是非之地,雖然並非自願,但識時務者為俊傑,我的確是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
高一剛開學時,安排座位是用身高來分,站在我前後面的二位同學,碰巧都喜歡打籃球,開學後沒多久我們就成為了很好的朋友,至今仍有聯繫,高一時我們就決定要一起考醫學院,日後一起打拼,而現在這兩位同學都是名醫,實至名歸。
高二下學期要填大學報考志願時,我刻意在最後一分鐘才繳交我的志願表,當時大學聯考分甲乙丙丁四組,甲組為理工、乙組為文學、丙組為醫農生技、丁組則為法商。當同學發現我填的是甲組時,問我原因為何,我支支吾吾地胡亂編了些不著邊際的推辭,最後還落了個“逃兵”的指控,被同學嘲笑是臨陣脫逃,而我也只能無言地吞下這顆滷蛋,不然又能如何呢 ?
我青春期的叛逆時間很短,嚴格說起來,大概也只有高三的上學期。我從小學到研究所,讀書考試對我都不是壓力,名次在前或在後、考好或考壞,對我也沒有什麼影響。高三上時,父親的冤獄在我心中的壓抑已超過了一年,那時老哥的情況非常糟,母親每天都得替他處理一些狗屁倒灶的事;高三開學後,學校的壓力突然增大,一大堆煩心的事碰到一塊,致使我對周遭的事完全不在乎,有時甚至會因反對而反對,藉以發洩心中積壓已久的無力感和怨恨。
高三開學前,我們選擇甲組的高二同班同學,被拆散用來補足其他班的人數,我被分到那班的數學老師是位名牌老師,在校外開授的補習班更是高朋滿座、一位難求。上第一堂數學課時,這位名師便言明他在學校教課的內容和在補習班教的完全一樣,如果班上有同學已經報名他在校外的補習班,請馬上退出,無需浪費補習費,也可以把機會讓給其他的同學,這個做法我很敬佩,是位清流,與當時其他名牌老師的授課方式,迥然不同。
只是好景不常,開學不到兩個月,我便成為這位名師的眼中釘,原因是在一個偶然的情況下,他發現我上課不但不抄筆記,還心不在焉地朝著窗外眺望,如此輕蔑的舉動,對於這位名師實為大不敬,把他氣得當眾對我跳腳大罵;殊不知我從小被父親罵習慣了,早已練成金剛不敗的特異功能,不想聽的東西,左耳進右耳出,不但能自動過濾,還會不時點頭示意,只是不管對方說些什麼,在我看來有如空氣,來無影去無蹤,霎那間便從地表上消失。如此的狀況,越來越糟,好在我考試的成績還算不錯,所以名牌老師想找我的麻煩,也有些困難。
某次數學課堂小考的前一晚,我得知父親在獄中的現況非常的差,多次因為身體不適而送醫急救,雖然都能及時脫險,只是每況愈下,最近一次被送醫急救的情況,比較嚴重,在醫院待了將近一週的時間,至今仍未出院。但母親卻是間接得知此事,而政府相關的單位則完全不予理會,視若無睹,看來只有在父親真有生命危險時才會聯繫家屬,基本無視我們的存在!
當天出門前,母親告訴我她早上會想辦法找些關係,看看是否能到醫院探視父親,倘如可以,她會直接打電話到學校替我請假,讓我提高警覺。那天的臨時數學小考是早上的第四節課,考試的好壞,此刻與我何干,既然快到午休時間,我在考卷上寫上名字後,就直接從後門離開教室,至於離開前需要得到老師允許一事,完全沒有從我腦海中划過,我就這樣無聲無息地從教室中消失。當時我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這一排只有2張桌子,應該有超過9成以上的同學,不知道我提前離開教室一事。
下次上數學課時,我被名師點名起立,他說他早知道我從不抄筆記,若我膽敢如此囂張,那麼上週的小考為何會繳白卷,現在我必須給他一個解釋。不巧那天我的心情格外惡劣,主要是因為上個週末,母親風濕的舊疾復發,全身動彈不得,而剛入伍的老哥在軍中又惹出了一些破事,由於母親無法親自去替他解決問題,我被迫身兼二職,一根蠟燭兩頭燒,往返台北和台中數次,精疲力竭,好在昨晚母親的身體稍微有些好轉,我才能稍微喘口氣。
怎知我一到學校上課,就被名師不分青紅皂白的質問,湖南騾子脾氣頓時爆發,我從座位站起來後,吊兒郎當地瞪著這位名師,一言不發,管你是老師還是名師,老子不想應答試卷,關你個屁事,你是你、我是我,我就喜歡繳白卷,你又能奈我如何;當時不流行比中指,否則我肯定當場就比給他看!
如此的挑釁,恐怕是這位名師從未遭遇過的事,當下便對我破口大罵,完全不顧及他是老師的身份,劈裡啪啦地罵了一缸子尖酸刻薄的話,罵到連我都有些驚訝,也不知他為何會有如此的反應,只記得在最後,這位名師對我說了一句異常苛薄的話,他說:“你這頭豬,殺了連刀子都要丟掉,因為是白刀子進、白刀子出,看看你這全身都是脂肪的胖豬,繳白卷也是正常啊!”說完後,這位名師得意地大笑了好幾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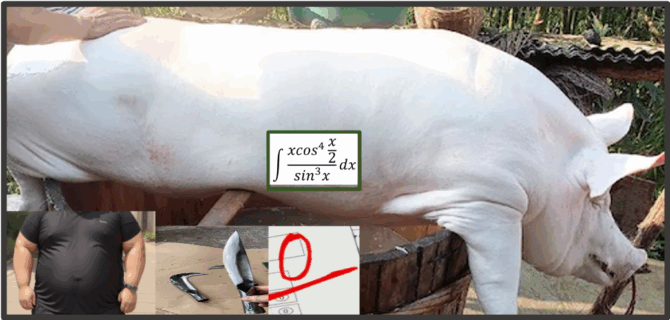
我當時不知該如何擠兌他,我從小就胖,被人笑是胖子或是豬,早已司空見慣,但被老師如此當眾的羞辱,還是第一次,我呆滯地站在座位旁,看著罵我的名師,在外人看來或許會認為我被罵是罪有應得,但那時我心中是五味雜陳,今天本想請假在家照顧母親,但她堅持我一定要去上學,縱使我覺得上學在當時已經沒有任何的意義,但為了不讓母親操心,我還是硬著頭皮到校上課。沒想到了學校,卻遭到老師如此般的嘲諷謾罵,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顫,難道此乃所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場面嗎 ?
只是想到日後我可能將多次面對如此被人辱罵卻無法反駁、還必須得默默接受的窘境,一股心酸逐漸湧上心頭,那份苦澀的滋味,當時我又能向何人傾吐呢 ? 至於後來課堂上發生了什麼事,以及我是如何脫困,早已從我的記憶中抹除,僅留下那句“白刀子進、白刀子出”的嘲諷在我心中迴盪,鏗鏘有聲。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很感謝這位名師,他的這句有意無意的謾罵,罵醒了當時的我,從那天開始我無時不在心中勉勵自己,事在人為,凡事得靠自己,深信假以時日,我定能靠自己的努力走出這個陰霾困境,而我的青春叛逆期,也就在那一刻,從我的人生中消失的無影無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