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老師
法律與我(1)
我大學唸國際關係,跟法律相關的必修課有法學緒論和憲法。當時只覺得上課無趣,旣是必修,唸完也就罷了。
退伍後考進外交部,分發到北美司從最基層的薦任科員做起。當時坐我隔壁的一位資深同仁正在處理長官特別交辦的「江南訟案」。他十分審慎,又有點兒神秘兮兮。
外交部委任理律、聯鼎等有名的律師事務所協助處理涉美訟案,他們提出的分析報告,在我看來水準平平,但大牌律師帳單每小時以新台幣9000元計,薄薄幾頁報告至少以三小時起跳,輕易超過我那時的月薪。
1988年我被派到華府工作,在這個全球的政治首都,據說街頭的招牌掉下來,砸到的路人每10個就有一個是律師。我也發現,我工作上接觸過的菁英份子包括國會助理和公關公司的說客,很多都是法律出身。當時有一本暢銷書 One L,描述哈佛大學法學院新生第一年上課的競爭情形,我讀了非常神往。
剛好馬里蘭大學在勞工部為聯邦公務員開法學導論的課程,三個學分,我報名成為班上唯一的外國人。期末考居然名列前茅,有點信心後便去考 LSAT,準備申請法學院的JD Progr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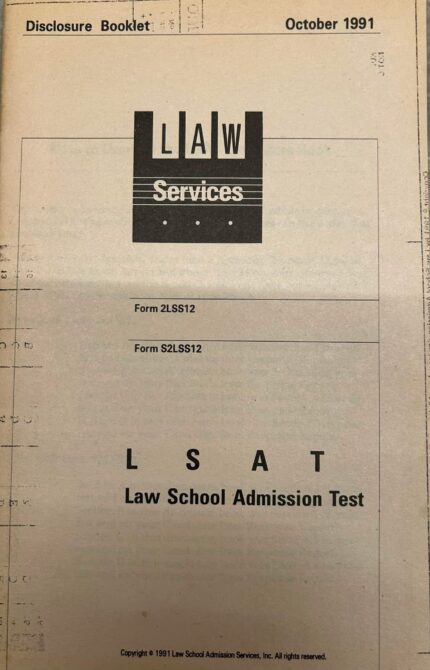
LSAT分數出來了,差強人意,大概可以上二級大學的法學院。但想到要讀三年,沒有薪水、學費很貴、第一個小孩才剛出世、壓力實在太大,只得放棄。
1994年調部,我決定改走國內路線,申請到條約法律司服務,獲派為第一科科長。這份工作主管條約、協定事項,與中央各部會的涉外單位互動密切,也經常要協同出差談判,標的包括避免雙重課稅協定、投資保障協定、漁權糾紛協定、甚至是軍備的後勤保養協定等。
兩年多的歷練,我對公法有了第一手的接觸,也培養了英文談判能力。當年Law School 沒唸成,當不了律師,如今做個可以管律師的科長,也不錯。更重要的是,這個轉變成為我之後職涯多元化發展的關鍵!
法律與我(2)
承上文,話說我在條約法律司任上經常協助各部會處理涉外法律問題,當時台北證管會與法國證管會簽訂一個合作備忘錄,產生草約用字明顯不對等的問題。戴立寧主委請我去商量,最後順利解決,於是派副主委陳樹前來挖角。一年後,我平調到財政部證管會,主管國際事務兼審查外資(QFII)。
這是我的職涯跨部會轉換的第一次,也是日後每隔三到四年就轉換跑道的開始。
證管會是證券市場的主管機關,規範有價證券的發行與交易,及衍生出來的會計師管理以及層出不窮的非常規交易,包括內線交易。我在證管會的四年主要接觸的法律就是公司法、證交法及其各種子法。36歲的我毫無金融背景,從頭學起,還蠻辛苦的。回想起來,我這一動頗為大膽。
2000 年我被調到財政部金融局第五組,監管在台所有外商銀行。這時期則是以銀行法和國際金融業務條例(OBU)為依歸。
2002年我國經過多年談判終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追隨顏慶章部長,代表財政部出任代表團參事。這三年我負責 WTO 有關服務業貿易的法律與協議(GATS),了解到在多邊架構下各種法規及判例如何運作和會員國間調合利益的折衝撙俎。更有意思的是,每天進出會塲開會,終於逐漸聽懂南腔北調的各種英文!
法律與我(3)
續前文,我在日內瓦的WTO代表團工作了三年後,接著去紐約及印度,這段時期的工作與法律比較沒有關係。
從印度返國後不久,有幸受到交通部長葉匡時的邀請,出任中華郵政公司董事長。環繞在郵政公司的最重要法規就是郵政三法(郵政法、郵政儲金匯兌法及簡易人壽保險法)。觀此三法,再看看郵局櫃檯的配置,便可以了解郵政公司其實是個準金融機構,金融業務及其相關營收佔了一半以上的份額。

2017年永豐金控出了狀況,我受託出任董事長。過去我曾經是金融監理官,現在成為被監理的對象。除了金控法外,與各子公司相關的銀行法、證交法、期交法、投信、投顧和創投管理條例等都是每天要面對的規範。三年下來我體會到,站在董事會的高度,經營三要事就是確實的法令遵循(Compliance) 、審慎的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和良善的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

2020 年我離開永豐金控,受邀到東元集團擔任董事會資深顧問,心想這份工作總算是比較輕鬆一點,沒想到又涉入喧騰一時的股權爭奪事件,雙方法律攻防激烈,硝煙四起。
這段期間我也兼任若干公司的獨立董事及擔任審計委員會成員,所處理的議案多與法律有關。
回顧我個人曲折多變的職涯,若非最初對法律產生好奇,並選擇離開舒適圈的外交部到證管會服務,後面的工作轉換都不會發生。我不是法律科班,過半的職涯卻與法律密切相關,這一切毋寧不是老天爺巧妙的安排。
(法律與我 全文完)




